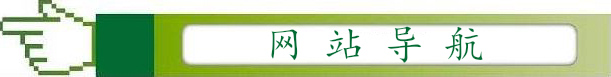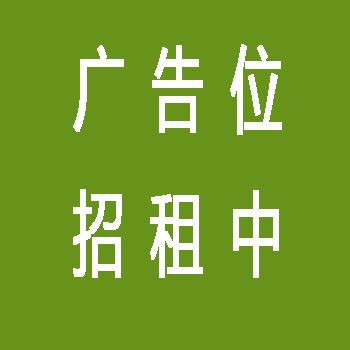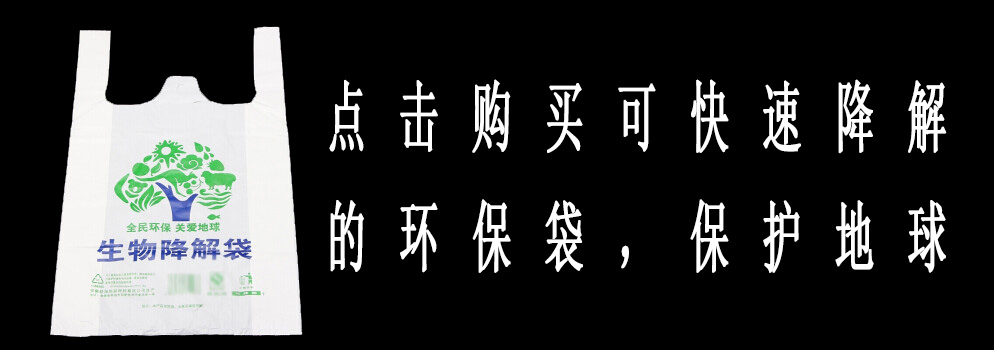读了《塞利格曼自传》,想问一个问题
塞利格曼能过关我们的教学考评吗?
塞利格曼在第一次讲《实验心理学导论》时,采取了他个人独辟蹊径的授课方式:"……我没有遵循传统的方式。我没有使用教科书,而是只用原创的期刊文章,并创建了我自己的授课模式,我希望这样能更好地把整个学科的重点内容传达给学生。我对心理学的热爱令学生着迷。我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授课主题,而这也深深地感染了学生。"这种教学方式竟成了我提升个人创造力的捷径。在授课过程中,我发现自己正在编织一个完整的心理学领域,而这个领域的结构在此之前是看不到的。今天,这个领域被称为“进化心理学”。在学生中,也出现了几个后来在美国心理学界的著名学者。
读到这里,我突然想起陈寅恪先生授课的情景:他"讲授佛经文学、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参考书,而讲其他课程,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,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,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了进来。下课时,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师休息室,他也不肯。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,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,写满一黑板,擦掉后再写。同学们都为他担忧,怕粉笔灰吸进肺里去太多,有碍健康,所以常常看到他快写满了一黑板就自动向前为他擦拭黑板。" “寅恪师每有一篇论文发表他一定把单行本带来,分送给听课的同学”。他每讲一次课,课前都要花许多精力和时间来认真准备,从不敷衍应付。陈寅恪坚持“三个基本不讲”,是他一贯坚持的教学原则:即书上有的基本不讲,让学生自己去读、去钻研;别人讲过的话基本不讲,不拾人牙慧;自己讲过的也基本不讲,除非必要,一般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。同一门课可以反复听许多次,因为每一次课,都有新的材料、新的发现、新的见解,内容不尽相同。同学们每听一次课,都会有新的收获,真正是百听不厌。
这些大师的授课方式却不能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大学讲堂上,定教材、定教案、定讲课方式,“三定”锁死了教师的创造性,也制造出“定型产品”的学生。在标准化课程的禁锢下,原本浩瀚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,并被称为”学科”。…… 客观上讲,中国高等教育的高峰之一出现在哪个国破家亡的抗日战争时期,培养出杨振宁、李政道、陈寅恪……以及提出“钱学森之问”的钱学森等大师们。话太多了,就用前几天读过的一句话来结束吧,"这些不是中国的教育问题,而是教育的中国问题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