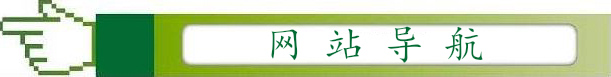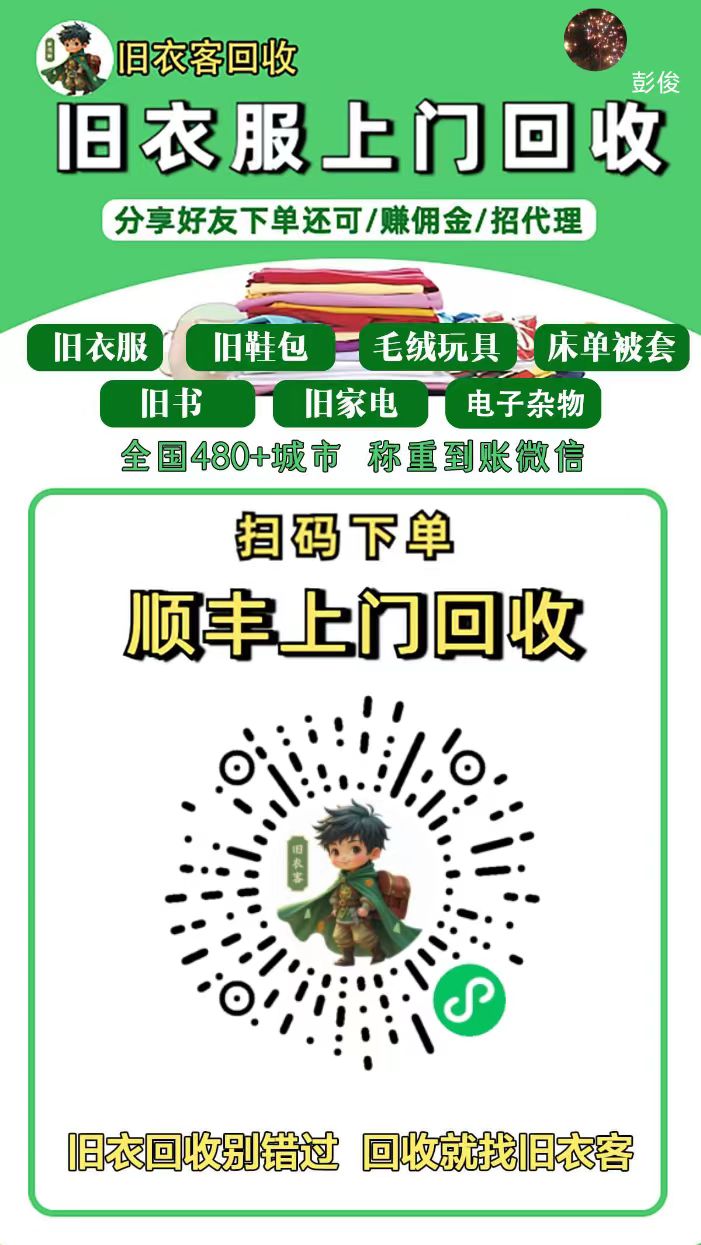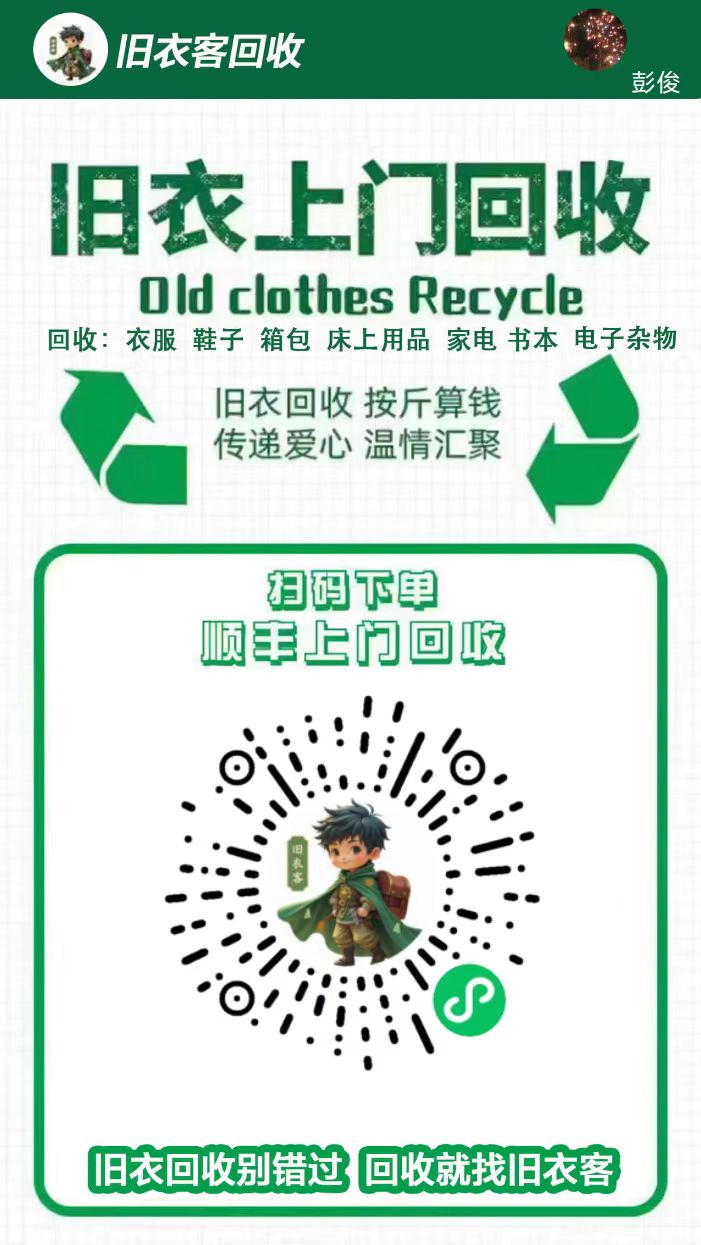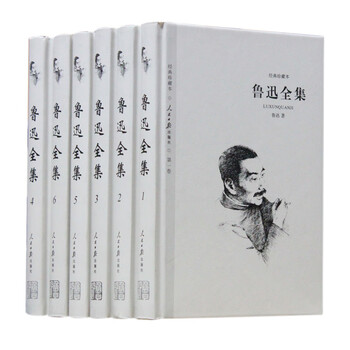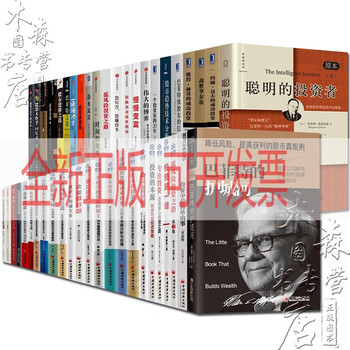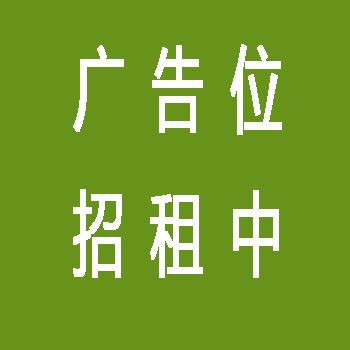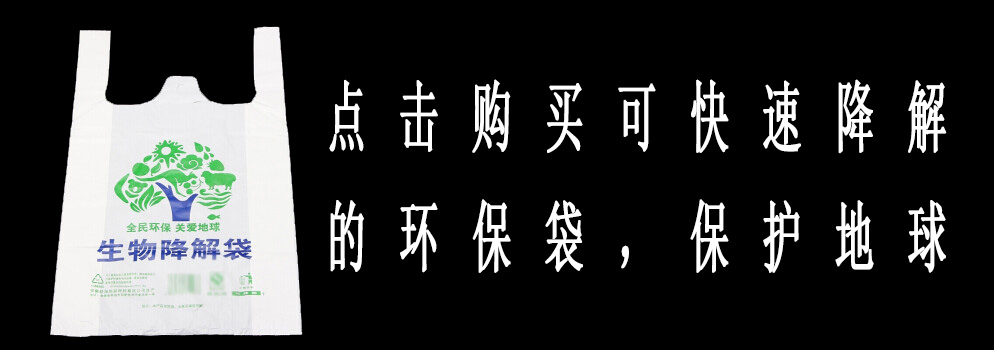“圣人韬光,贤人遁世”,“遁”在现代生活中尤其显现出一种有心无力的内心奢求。当然如果能学得道家仙术,除了大家都知道的《封神榜》里土行孙的土遁之术,“金木水火土”其实都是可以遁的。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,想来也许是起了“遁”心,借了这些印刷的纸张,溜出去长长地透一口气。想到这里,便瞎取了一个书名,叫做“且借纸遁”。
而我一下子就被《且借纸遁》这个瞎取的名字给吸引了,在微信读书看罢此书,果断下单买了本纸质版。葛先生1994年至2011年间泛览一百五十余种“闲书”所做的笔记和摘抄,遂成此书。
此书满足了我了解历史学家都看些什么书的窥私欲。《且借纸遁》读起来很容易,也很不容易。每篇文章篇幅不长,有的甚至寥寥数语。毕竟是学者,看的部分书籍艰涩难懂、枯燥无味,以至于这类书的笔记也让我脑子一团浆糊。当然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愚钝,于是先在目录里挑选了几篇喜欢的话题阅读,葛先生的介绍、摘录以及点评,都让我耳目一新甚至令人茅塞顿开。
且举一例,读《郑孝胥日记》(中华书局,1993),葛先生颇为感慨:一百年的事件真是不短,说到前清的人事,仿佛已经遥远得很,有时候想起来,不由得会把它当了“古代”。可是读这本日记,却又颇为恍惚,好些事情和场景好像就在前天或大前天。
光绪十七年(1891)郑孝胥出使日本(他先任筑地副领事,后二年充神坂领事)到二十年(1894)归国这一段时间里写的东瀛日记。日记里郑氏对日本的新政大为不屑。尽管身处变法的日本,仍长袍马褂,过着如同国内士大夫的生活,狎妓听戏,吃茶饮酒,似乎乐不可支。一天到了浴室,见“裸体赤立者右男而左女,俯仰自如”,倒也觉得怡然。
葛先生说:这大概是甲午之前中国文人士大夫的风习?…… 要到了甲午一战之后,他才在日记中有震惊和愤怒。……看来,不变的是山川,常变的是人情,更容易变的是时势,难怪古人说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。
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,如果不是看了葛先生的介绍,根本无从知道并些许了解了郑孝胥是何许人也,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“知识分子”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。
葛先生所泛览的“闲书”当中,有些书便进了我的书目,我也开始寻找他的其他著作。遗憾的是这些书,有不少是日本、香港、台湾等地的出版物,遗憾的是葛先生的一些著作也没有在国内出版。于是我忽然多了一个向往:未来的旅游,我也许该找机会住在某处目的地的某个图书馆附近,每天去看一些我从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书。
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