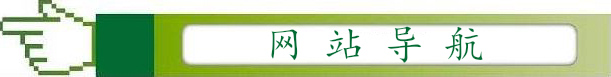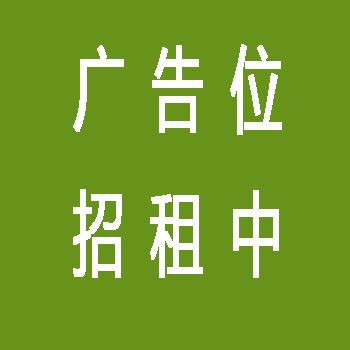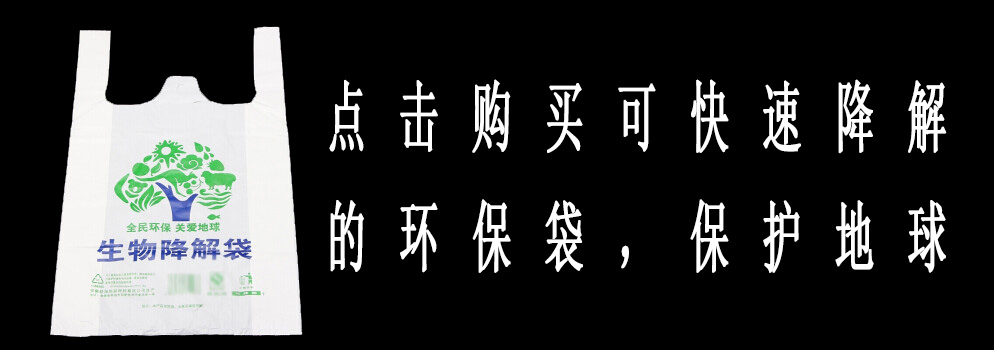‘秦腔’又叫‘乱弹’,可以说是我国戏曲的鼻祖,它的音调激越高亢、节奏鲜明,表演朴实、粗犷、富有夸张性。流行于西北地区尤其是三秦大地。
贾先生的作品我看了几本,大都描写的他生活且熟悉的那片土地。这部作品以‘秦腔’为书名,其义自明。鲁迅先生一生忧国忧民,在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和对命运深感无力的时候就呐喊,以便“揭出病苦,引起疗救的注意”,同时也是“未能忘怀当日自己的寂寞悲哀,所以有时候不免呐喊几声,聊以慰藉那在奔走的猛士,使他不惮于前进”。而贾先生也吼起了“秦腔”,那一声声苍凉的余韵中,有着深深的对失落的农村文化的同情,也为逝去的记忆立起了一块碑。
社会在日益的发展前进,人们抛弃传统的价值观念,开始以金钱至上作为自己的内核,致使社会风气物欲横流。而被抛弃在社会边缘的农村文化,却也正在土崩瓦解。村民们丢了锄头,卷了铺盖,纷纷奔向大城市,他们以为走向了康庄大道,明白过来时却发现自己处在了农不农、工不工的尴尬境地,他们内心也逐渐的遭受到了冲击,变得苦闷茫然。农村的文化传统正在凋落,农民们既丢了根,又找不到新的出路,因此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。
贾平凹的《秦腔》吼出了这种失落的腔调,深深的震撼着我的内心世界。小说把鸡零狗碎的家长里短、生活情节交织到一起,展现出了最为真实的农村生活图景,也展露出本质的精神空虚。社会转型时期,农村被推着向前走,传统的一切变得面目全非,而自身又跟不上社会的步伐,处在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里,为农村人,或者说为社会上的边缘人找到一种出路成为当务之急。这种出路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保障,更多的是对内心世界的一次重组,让人找到一种适应目前存在状态的一套价值观和生活法则。写到这里,我想起了之前读过的美国作家万斯的《乡下人的悲歌》,他对美国当时的‘乡下’出现的问题表现出和贾先生同样的担忧。不同的是他表现的只是几十年前的美国东北部铁锈地带,而贾先生表现并担忧的却是我们大部分农村的问题。
中国一味的追求壮大,在疾步向前走的同时,文化世界就逐渐被瓦解。或许人们隐隐约约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处境,但也顾不得找回失落的东西,就随波逐流的一直往前。处在潮流之外、不合群的这批人,就每天深受着精神上的折磨,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吼上几声,可这声音不吼还好,一旦吼了出去,在荒山蔓草四下里传来悠长的回声,更加的让人空虚寂寥。
所有的呐喊都是一个人的寂寞,在当下快节奏发展的社会里,没有人会停下来去听你的呐喊。他们早已失去了理解这种呐喊的能力。你所唤起的无非是来自于广阔空间的回应。乡愁,不在人们心里,而成为文学上的说辞。乡愁是文化中的最为基本的情感,而丧失掉了乡愁的人,也就如同孤魂野鬼,找不到一种归属,成为失落的一代人。
值的庆幸的是,现在至少还有人吼两声秦腔,随着这些人逐渐逝去,未来的年月里还有人能吼秦腔吗?这一切都是未知的。
文化是什么?文化是根,是一种精神,是一种信仰,如果失去了文化,我们做人的意义又何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