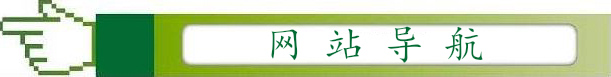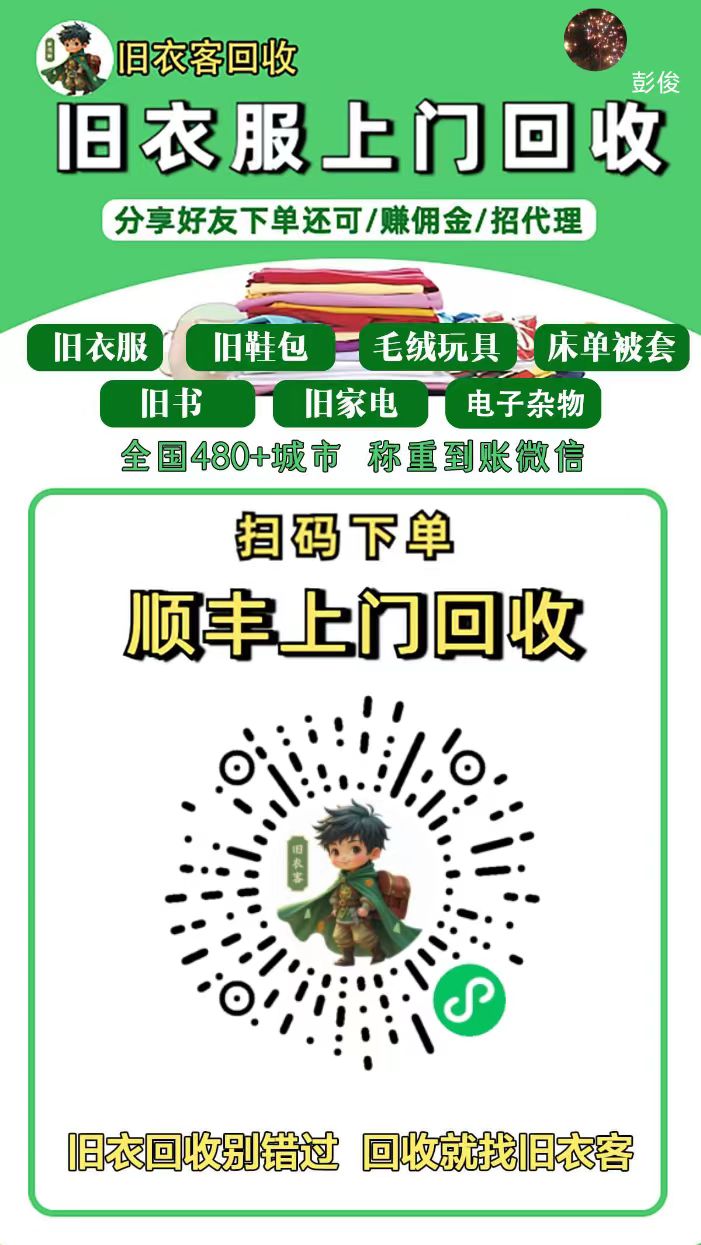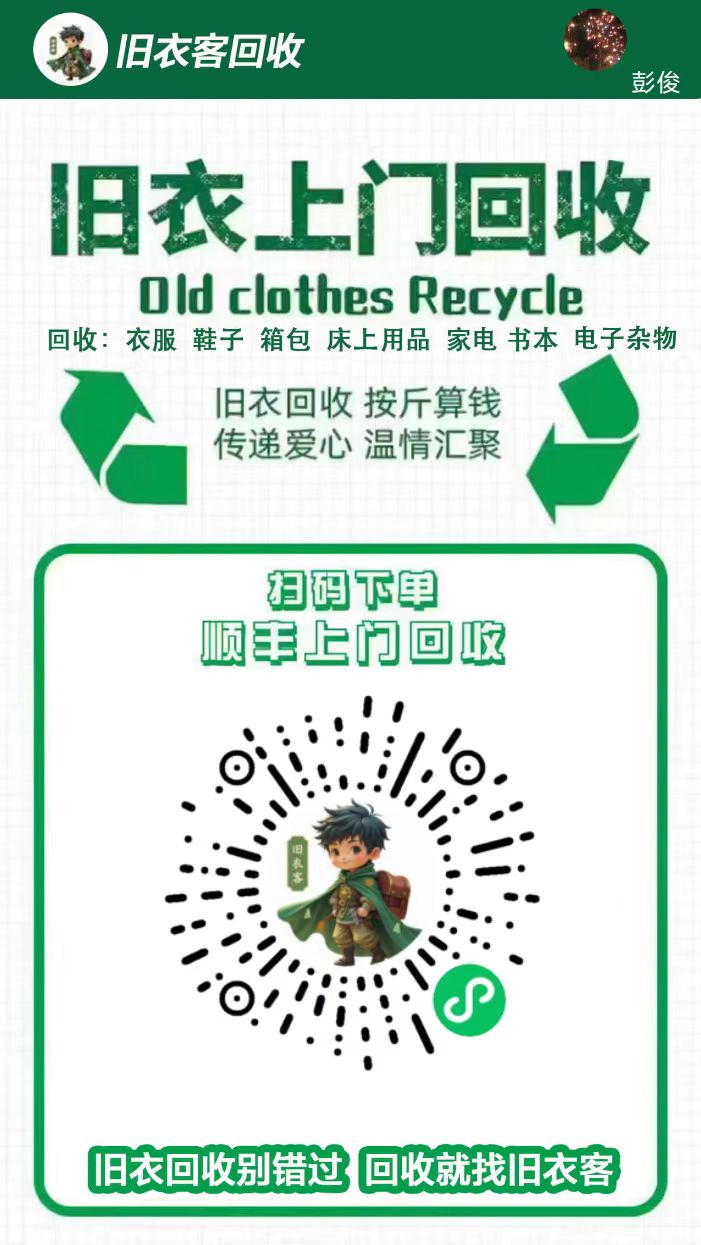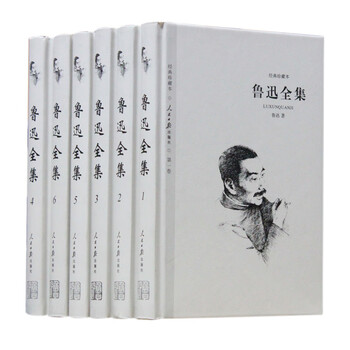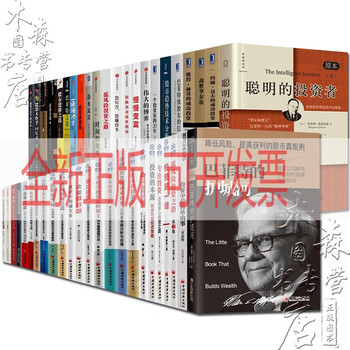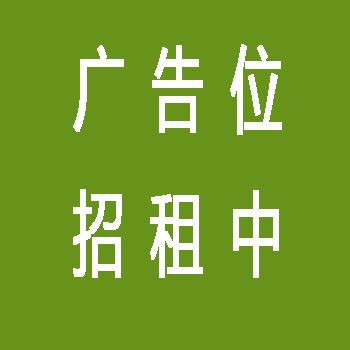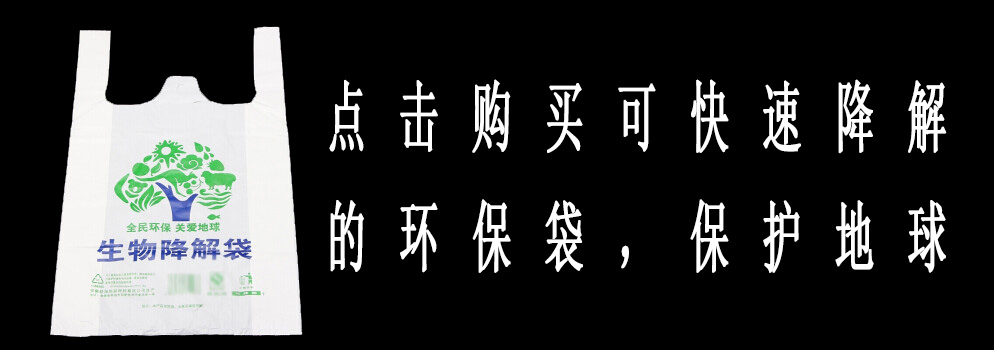他可能是文学史上最受争议的一位。
木心在《文字回忆录》这样综述:
当时真正理解他的人(指文学家)很少。别林斯基受不了他对人性剖析的无情。后来的高尔基以为他是恶的天才,中国则由鲁迅为代表,认为他是残忍的。
面对这些大师的评价,木心意味深长地回应一句:
要去评价一个伟大的人物,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物?这是致命的问题。
这位伟大的人物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。
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,很多人都会将之与托尔斯泰比较;两位同时期的俄罗斯文坛巨匠,可谓一时双璧,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据着最巅峰的位置。
如果说,托尔斯泰的文字是明媚鲜艳的,字里行间散发着馨香之气,迎面而至的是徐徐的暖风;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则是阴郁黯淡的,和着底层的汗腥气与袜子味,混着小酒馆醉醺醺的喧闹声和不入流的骂腔,透出的是鲜血淋漓的惨淡与不可言喻的荒凉。
陀氏似乎是把地沟沟里的一切都挖将出来,散发阵阵恶臭,叫人忍无可忍却又欲罢不能,因为那地沟正是在人内心深处。
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的文字,重新定义了深刻。读陀氏的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因为他不仅需要你动脑,更需要你动心。
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便是带你踏上一场心灵的朝圣之旅。
《罪与罚》是一个推倒巴别塔的故事。
什么是巴别塔?
上古时代,天下万民聚集,为造通天塔,荣耀自己的名;耶和华神降临,将他们分散各地,变乱他们的口音。从此,那座城便称为巴别。
巴别塔的工程止息了,但人类修缮巴别塔的野心从未止息,巴别塔的故事从未止息。
《罪与罚》的巴别塔便是其中之一。然而,它既不是秦始皇追求的长生殿,也不是野心家追求的帝王术;它的根基只是一个问题——人为什么不能僭越到伦理道德之外行事?
正如极为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尼采如是宣告:上帝已死。
尼采的意思并不是指上帝真的没有了,消失了。他只是质疑,普世的基督文化道德体系,是否还能约束所有的人;是否还有另一个更超越的规范,他在寻求新的超人体系。
尼采宣告:上帝已死,上帝的位置还在,虚左已待。
于是,一个住在鸽子屋、穷困潦倒的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,没有足够的经费完成学业,家人为了支援他读书也已经山穷水尽;他突发奇想,如果是伟大如拿破仑,在这样的处境下,他会如何?他在内心构思了一套无懈可击的超人理论。
他实践了,用斧子砍死了两个无辜的女人。他赞叹,我可以僭越!这便是他所造的巴别塔!